阳海清编委在《荆楚文库》工作委员会暨编纂出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
发布时间:2013-10-25 来源:荆楚文库 阅读次数:
阳海清编委在《荆楚文库》工作委员会暨编纂出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
(目录学家、《荆楚文库》编委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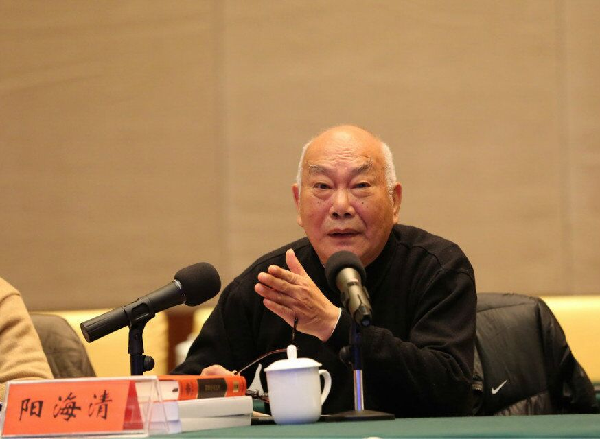
《荆楚文库》编纂工作启动,已经一年挂零。目前所面临的形势,可以用“卓有成效”与“任重道远”八个字来概括:回顾过去,卓有成效;展望未来,任重道远。
(一)
一年多来,在省委省政府的悉心关怀下,在工委会和编委会的直接领导下,在总编辑的正确领导下,在编辑部的精心安排下,在相关学者的共同努力下,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,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。其中,足以称道者有:
(1)确立编纂宗旨。
众所周知,编纂《荆楚文库》是我省文献整理的空前伟业。面对源远流长的荆楚文化和汗牛充栋的古今文献,编纂者的第一要务就是要高瞻远瞩、高屋建瓴,确立《荆楚文库》编纂宗旨。古往今来,凡从事大型和巨型文化工程,莫不如此。记得在编纂《续修四库全书》时,几经讨论,才确立“理清近三百年来学术文化发展源流”为主线。我们确定“全方位搜索、整理湖北历史文献,建立完善的研究湖北的资料系统,以深入认识湖北地域特色,传承弘扬优秀文化,促进湖北文化繁荣发展”作为《荆楚文库》编纂宗旨,既符合“古为今用”、“与时俱进”原则,又符合湖北历史文献发展状况。
(2)规定编纂范域。
在《编纂出版方案》中,明确提出“三类作者”和“两类文献”是《荆楚文库》的“编纂范域”,充分显示了编纂者的卓识和睿智。这是基于对荆楚文化发展历史的准确把握,对湖北文献现存状况的完整掌控和对古籍整理原则的深刻认识。因此,它是科学的、可行的、能够掌控的。
我个人认为,将“民间文献”和“出土文献”中“有学术价值者”列入选辑范畴,则尤见识力和尤具创造性。通常整理地方文献多将眼力聚焦于传统典籍而少有顾及至此者,而此二类文献不唯是地方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,而且是亟须抢救和整理的内容。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,如果在这两方面投入相应精力,《荆楚文库》便会拥有自己独具的特色。
(3)设计总体构架。
编纂大型和巨型丛书、类书,有如构建高楼大厦,必先拿出“扩初设计”图纸。《荆楚文库》确定分为“文献”、“方志”、“研究”三篇,《文献编》按时代,《方志篇》按区域,《研究篇》按主题来分别序列各自所收文献。这一“扩初设计”,堪称匠心独运。第一,灵活地运用了文献分类原则;第二,有效地覆盖了所有入选文献;第三,恰当地处理了抢救、保护、整理、利用四者之间的关系。
(4)编就工作书目。
这是在从事巨大型文献整理工程中最琐碎、最具体、最麻烦的一个工作环节。编辑部的专家们在广泛搜罗文献和深入听取意见的基础上,以不到一年的时间,即编出了《荆楚文库》书目,速度异常,成效显著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,国内集中了一批著名学者、教授、大师来编纂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,仅搜访和确定入选书目就花了近十年时间,可以想见此事之难度。虽然不能说《荆楚文库》书目已经至善至美,但其作为一份工作书目则是成功的,一是框架初具,二是要籍毕陈。
(5)提出整理方案。
有关《荆楚文库》编纂和文献整理方法,目前尚未出台规范性文件,但在工委会、编委会、编辑部领导和成员的讲话和文字中,在省内外专家、学者的意见中多有涉及,有的似已形成共识,为拟制相关细则、条例打下基础。
过去一年,《荆楚文库》编纂从理论阐发到具体实践,事无巨细,还做了大量工作。仅就上述五端言之,谓其卓有成效,绝非虚妄之言。
(二)
俗话说,良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。其实,惟有完美的收官才是胜利的全部。《荆楚文库》编纂,初战告捷,后续工作更为艰巨。为获全胜,提出以下建议,谨供参酌。
(1)注意抓好微调。
大局确定以后,微调不可避免,它会贯穿于整个编纂过程的始终。微调的内容包罗甚广,涉及品种遴选、版本择定、篇幅全残、校勘粗精、序列次第甚至启动迟早和操作细则。微调要及时,宜早不宜晚;微调要精准,不可随意为之。已经编就的《荆楚文库》书目只是一份工作书目,离《遴选书目》、《选辑书目》尚存一定距离,这就给微调留下了一定空间。新近,我草拟了《“方志编”编纂工作整体方案》,将应辑入之方志分成十类,其中有四类“必收”,四类“不收”,两类视情况酌定,并非绝对照搬《荆楚文库书目》,而是有併有删。
(2)拟定操作规程。
《荆楚文库》容量大,品类繁,种数多,必须分工整理,必然出自众手。编纂巨型丛书之大忌,最怕随心所欲,自乱规章。尽快拟定操作规程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不二法门。
(3)坚持慎改书名。
擅改书名,易在学术上造成混乱,重蹈明人编书覆辙。《荆楚文库》决定采用“以人系书”之法,将会编出许多“独撰丛书”(或曰“自著丛书”),并规定其内容仅限于诗文集者称《×××诗文集》或《×××诗集》、《×××文集》,其内容跨部者称《×××集》,取此新名以统括之;若原有集名,此次并无新增内容者,仍取其原书名。统一如此操作,并无不可。兹所强调者,收入新编各集之子书,不宜随意更改原名;若原属散篇,系本次搜聚成编,自可循名责实,冠一新名。
(4)掌握文献状态。
一部文献问世后,在几十、几百甚至几千年流布过程中,通常会呈现出四种状态,即生成状态、流播状态、揭示状态和庋藏状态。今天我们来整理某部典籍,宜对其四种状态作相对全面的了解,如此方可减少或避免疏失和错误。
(5)择优选用底本。
凡一书有多个版本,版本选择是否妥当,成为古籍整理成败之关键。务必从时间早晚、篇帙全残、校勘精粗、次第顺乱、品相好坏等多个角度对其作全面审视,仔细辨析,择优而用。一般说来,由作者自编且生前付梓者,其准确性较为可信;作者殁后,尤其亲属、同僚、弟子、乡亲搜集成编者,其完整度较高;由知名学者校定者,其学术性较强。但不宜偏执于一面,宜作全面考察、辩证分析,方可作出相对准确之判断。网上材料,除影印本可信外,大多有疏漏讹误,务必慎用。
(6)切忌弄成拼盘。
古人编纂图书,极讲章法。单以篇章次第言之,即往往有其严密的内在联系。目下古籍整理,有一种不良倾向,动辄打乱原著重编,弄得面目全非,似乎不如此不足以称“整理”。其实不然。有如家装,东拆西补,看似改正了原装之不足,实则扬弃了原设计之优点。愚意以为,《荆楚文库》编纂,应遵循古籍整理的一些约定俗成原则,尽量保持文献原貌,不做拼盘。建议于整理时,先择定底本,再参校众本,发现歧异,在底本上出注或作《校勘记》;发现遗漏,可作《附录》、《补遗》殿于书末。须知“注释”、“校勘记”、“补遗”、“附录”之类,能给整理者提供广阔的活动空间。
(7)万勿臆改原著。
一名有责任心的学者,自会对前人成果常怀敬畏,纵有异议亦会先思考原作者为何会如此,再正其非。但有个别人胆子特大,随手臆改。前几年影印出版的所谓《[嘉庆]郧阳府志》就是一例,不唯臆改了书名,撤换了版心,而且随意填补不清晰之文字;尤令人费解者,以其底本《湖广图经志书》又名《湖广通志》,便误为二书,竟然将同版之书一依本名一据又名同时影印。古籍情况复杂,若不细审细辨,便容易出错,《荆楚文库》务必避免重蹈覆辙。
(8)统一整理用字。
《荆楚文库》之《文献编》和《研究编》拟用整理本,这便存在一个统一用字问题,究竟是用现今规范简化字,还是用民国间通行繁体字,或者照采原书所用字,三者各有利弊,但需作出明确规定。
(9)重视封面格式。
就我所知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部分品种付印后,发现书名页所题文字和格式不一,在京编委曾全体赴厂订正。要确保书名页的规范、准确。这看似小事,也马虎不得。
(10)防止自我拔高。
这主要表现在整理者加工方式和加工程度的签署上,一定要实事求是。有的作者喜欢自我拔高,要防止。
(11)关心编纂人员。
细化鄂政办函〔2015〕45号文件第六条实施办法。各有关部门宜为参编专家办理返聘,让其真正享受与在职人员同等待遇,在工资福利、职称晋升、职级评定、考核奖惩等方面一一落实,从而体现党和政府的关怀。
《荆楚文库》编辑部的诸位先生都是资深行家,上面所述或有班门弄斧之嫌。唯我所列各点,均有事实为证,意在提醒,免走弯路。倘能知我此意,则是所至祷。